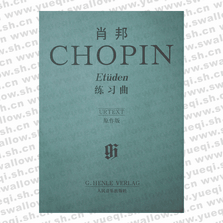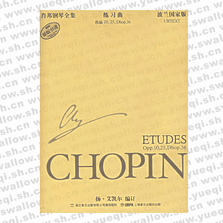肖邦作品原始版本的编辑所面对的远不是鉴定无数原始资料的简单任务。即使能得到全部资料,也很难在简单的浏览后确定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方面,莫里斯J.E.布洛的著作《肖邦――作品的年代次序索引》(伦敦,1960年)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肖邦没有以整套的意识来构思他的练习曲(包括圆舞曲、玛祖卡舞曲及夜曲等),只是在后来才把众多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按类收集。作品系列的作品第10号和作品第25号就是按此法分类。
有些练习曲可能是间隔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如作品第10号写于1829年至1832年间,作品第25号写于1832年至1836年间,另3首没有作品号的写于1839年。有些作品留有多种版本,随后它们都被作曲家作为呈献的作品。为此某首曲子就会存在数份手稿版本,每份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区别,结果,甚至连这些作品的手稿资料也不一致。
同样很困难去收集不同的印刷版本。由于肖邦的经营意识绝非一点没有发展,他也安排很自己的作品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同时出版。虽然肖邦还总是信任抄谱员,但偶尔也会出现出版者为自己制作雕刻版的情况。如他的朋友朱里安・丰特纳就因他的笔迹与肖邦有惊人的相似而著称。
为此留给了后人一项鉴别个别抄谱员所写的笔迹和判断他们版本精确性的研究任务。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不同国家出版的首版之间不同之处的对照也许对此有所帮助。
乔治・桑谈到过肖邦非常细致谨慎的创作习惯。然而不应忽视的是,他的敏感和异常即兴的天才素质,使他总是易于受到油然而生和直觉创作冲动的影响。因此原稿资料所呈现的分歧不应总是看成是错误或者疏忽。他们也许来自于肖邦另一次的创作记录。同样,首版之间音乐上的不同不能都看作为雕刻制版过程中的错误或疏忽。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有另一份资料(也许你现在看不到)已经作为某一雕刻版的原稿。由于原始资料的如此不确定性,所以不可能去确定在首版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它们或许产生于对原稿深思熟虑的修改,亦可能是音乐上的变体。另一方面,因有如此广泛的原始材料,在选择特定文献时个人喜好的指导因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与一致的原始资料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练习曲原始资料的收集是很困难的。
为了达到一个近乎一致的资料基础,编订者已经通过比较首版与雕刻版问那些发现在手稿中的(若不能总是,至少经常能找到)记录,试图去发现该手稿是否已成为某一个首版的雕刻版的原稿。虽然这种努力只有部分成功,但它却是收集和鉴定原始资料的一个可行办法。这是在对现今版本做修订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例如,假如某部手稿作为某个首版的制版原稿的关系是明确的,或者是不确定的,那么对照手稿与首版间的一致或者任何变体.也许就能清楚是否是印刷排版上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手稿与首版之间没有这种关系的证据,那么首版中的不同之处很有可能起源于另一迄今未知的手稿,也有可能肖邦在出版者的制版完成之前对手稿作了某些有意的改动。在这些 情况下,有关哪些资料应作为现今版本的基础问题并不适应于全部作品,而是每首曲子应分开单独 考虑。
作为作品第10号可得到的手稿,早期的第2首的抄本和第3至第12首的手稿可看作为肖邦的原稿,而第l首和第2首可能出自于肖邦的姐姐之手。通过雕刻版的注释来判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手稿第(3、6、8、10首)可能属于由莫里斯・施莱辛格于1833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首版的原始资料(不是如潘德雷斯基声称的由勒穆瓦纳编订,他显然用了后来的版本)。除上述资料还有另外的手稿参考材料也被作为此版本的基础材料,其间的关系部分是确定的,还有的部分至少很像法国首版的原始材料。由基斯特纳编订的德国首版是与施莱辛格的紧密合作之下产生的。就第3首练习曲而言,除了上述资料,另有一份资料是纽约的R.O.莱曼收集的手稿可供参考。
对于作品第25号来说,根据华沙肖邦研究会的克雷斯塔纳・科贝兰斯卡所称,只有现在的作品第25号波兰手稿的第1首和第8首是原稿,而其余作品的手稿是丰特纳或者其他抄谱员的抄本。由于波兰的资料来自于布莱特科夫・哈特的档案,他们可能也是1837年由布莱特科夫出版的德国首版的制版原搞。在此,两个版本的原始资料倒是一致的。由雕刻师制作的五线谱部分与原稿一致,在德国首版中有少数例外(第3、6、7首),然而这是仅对第1至6首而言。到此为止,对于剩下的作品来说什么都没发现,所以,就第7至12首来说,如在标题页所示的,现今的版本是根据后来(1846年以后)的版本基础上编订的,并且因为此原因,他们不能被看做同样的权威性。事实上,这个后来的版本可能是与首版结合的修订本,这个德国首版的第二部分以及全部作品的法国首版,必定基于其他参考资料,所以只能有所保留地被参考。除了以上,还有另外的数份参考资料,如:第1首的另一份手稿,第2首的手稿,第4首的另一份手稿的1―20小节(以2/4拍子记谱)及第4首手稿的最后1―22小节。
肖邦创作了3首以“为技术而技术”的没有作品号的练习曲,由莫施莱斯和费蒂斯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因此,供此版本所参考的手稿必定已作为雕刻版的原稿。而且这些练习曲出现在由同一个出版商于1841年出版的某一版本和柏林的A.M.施莱辛格的合集“钢琴纪念册”之中。
在编订过程中,编者很明确上述材料的原始出处,并觉得更多的发现和修订仍有可能。在这种
情况下,制定一个原始版本的任务要求考虑每首练习曲的各自情况。
相对于一般采用的G.亨勒’韦拉格的原始版本,相当数量的原先指法以常见形式保留在此曲集中,那些由编辑所加的指法用斜体标记。不仅主要资料的指法被保留,而且除少数例外的所有传统指法同样保留,因为它们代表了由作曲家所设定的重要的演奏指导。
那些很仔细地标记在手稿中的踏板标记,在编订时仅取自于主要的材料,因为原先的踏板可能已不适应于现代钢琴的演奏(乐器更大、声音更响、演奏厅更大)。今天,演奏者必须比资料中所标的更频繁地更换踏板,并且比起肖邦所标记的,在演奏时需要在更多的段落使用踏板。有时.快速的段落还需通过轻盈的触键和模拟那个时代乐器的单薄音色来演释。
至于资料中任何能够清楚区分的不同断奏记号(圆点与楔形),编订者力图保留原先的标记。但是,原始资料中对这些记号的使用有时看来非常含混,在很多地方意图不甚明确。在同一首练习曲中,对两者的使用非常矛盾,有时模糊了两者的区别。
编辑衷心感谢以下个人和机构慷慨提供有关原稿资料的照片副本:巴黎的M.奥尔富莱德・科托特、伦敦的安东・赫德利先生、华沙的肖邦协会、纽约的欧内斯特・谢林、瑞士的科克・弗洛什姆。编辑尤其感谢以下个人的各种信息和建议:维也纳的包罗 巴杜拉一斯科达先生、华沙的克雷斯塔纳・科贝兰斯卡夫人和佐菲亚丽萨博士、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布卢默博士和施吕赫特尼、英格兰马尔伯勒的莫里斯J E.布洛先生、巴黎的M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夫。
埃瓦尔德・齐默尔曼
(徐德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