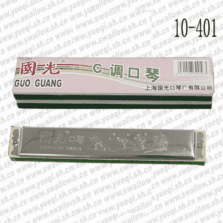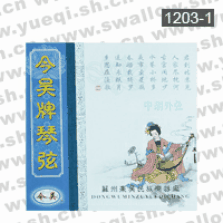我自幼喜欢音乐,是由口琴引发的。刚开始时用口琴吹奏一些世界名曲,跟着买回来唱片欣赏,阅读有关音乐的书籍,参加音乐会听交响乐曲,中学时又跟一位在澳门绿邮电台当第一小提琴手的李先生学小提琴,对音乐的喜爱简直达到如痴如醉的地步,甚至平常走路时也在哼唱。那时喜欢的是西洋古典音乐,如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对外国名曲朗朗上。对外国名演奏家也很崇拜,对中国的音乐却是看不起的,觉得中国音乐落后,尤其是广东小调,认为是下里巴人,俗不可耐。
如今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十多年, 比以前在澳门、香港居住的时间还长,对中国音乐的感情也由此而改变了。尽管我还是那么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年年预订套票去听卡城爱乐乐团演奏交响乐。可奇怪的是,偶然吹吹口哨,不再是《蓝色多瑙河》,而是红线女的《昭君出塞》;晚上睡前听的并非《萧邦夜曲》,而是石叔诚弹奏的《平湖秋月》。家乡的旋律令我感到无比亲切、无限眷恋,这是文化的回归。少年时代听到的“下里巴人”在我脑里中再现,变成了“阳春白雪”,回味无穷。
如今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十多年, 比以前在澳门、香港居住的时间还长,对中国音乐的感情也由此而改变了。尽管我还是那么喜欢西洋古典音乐,年年预订套票去听卡城爱乐乐团演奏交响乐。可奇怪的是,偶然吹吹口哨,不再是《蓝色多瑙河》,而是红线女的《昭君出塞》;晚上睡前听的并非《萧邦夜曲》,而是石叔诚弹奏的《平湖秋月》。家乡的旋律令我感到无比亲切、无限眷恋,这是文化的回归。少年时代听到的“下里巴人”在我脑里中再现,变成了“阳春白雪”,回味无穷。